燕草如碧丝
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
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
何事入罗帏
不知怎么,从起床这首诗就一直在脑子里回旋不去。还是把它记下来,做成一个不相干的题目。
当君怀归日
。
。
。
是妾断肠时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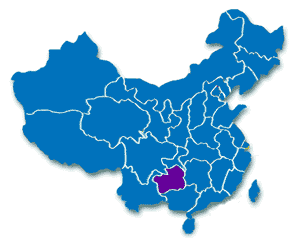 贵州的好处我知道的实在不多。苗寨对歌什么的都只是听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去也只去过龙宫和黄果树瀑布,以及贵阳附近的几个公园。然而贵州整个处于半开发状态,从工业区往外走出几里路就是长满松树的山 - 不过秃山似乎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倒从来没有太遗憾过。另外比较不好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太缺乏浪漫主义精神,风景对我的吸引远没有吃穿来得严重。
贵州的好处我知道的实在不多。苗寨对歌什么的都只是听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去也只去过龙宫和黄果树瀑布,以及贵阳附近的几个公园。然而贵州整个处于半开发状态,从工业区往外走出几里路就是长满松树的山 - 不过秃山似乎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倒从来没有太遗憾过。另外比较不好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太缺乏浪漫主义精神,风景对我的吸引远没有吃穿来得严重。
刚到贵州的时候,跟几个大胆的同学放学后偷偷跑去山里,说是樱桃熟了去摘樱桃。几个人大概走了很远很远,中间还迷了路,后来也不记得是怎么回去的了。樱桃并没有找到,见到了一棵据他们说是李子的树,非常高,我们之中唯一一个会爬树的努力攀着树枝摘了几个青青的象枣子的东西下来,咬开来,并没有什么味道,只略带一点苦涩,中间的核还是白的。其他的印象,就只剩满眼带着湿气的浓绿和深棕,以及不时在草丛中发现的鲜红的小浆果。据他们煞有介事地说那叫蛇果,本来果子应该是白色的,被蛇爬过后变成了红色,并且生了毒,吃了就会死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但当时却是将信将疑的,觉得这么漂亮的果子竟然不能吃实在可惜,但为了生命起见,还是非常不舍地把将要放进嘴里的果子扔回草丛,并告诫自己回家一定要好好洗手,以免手上残留的毒把自己毒死 - 我那时候已经看过了射雕,是知道一些下毒的要领的。
贵州人对吃的热爱远远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很多省 - 不知道比四川怎样。贵州很多吃法实际上源于四川,但经过他们的潜心研究,往往能够推陈出新,翻出很多新花样来。贵州人在吃上的用心,大概可以跟日本人在科技上的用心比一比。大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该算是酸汤鱼了吧。我并不清楚酸汤鱼的来历,只是猜测,因为四川的酸菜鱼是最先打出招牌并一下子普及全国的。我当时人在贵州,也大约知道饭馆们在酸菜鱼热潮后换了酸汤鱼的牌子。希望没有因此诋毁贵州人的创造力。贵州人做四川菜,总也能够八九不离十,但他们并没有满足在模仿的基础上,而是在多次试验之后稍减四川的麻,再加入贵州的特色:酸。据说,酸汤用的是贵州本地的酸白菜(想来是跟四川酸菜不一样的),酸西红柿,和酸辣椒(应该是糟辣椒吧,类似于湖南的剁椒)等三味酸料,加入鱼骨(大概还有猪骨鸡骨和大量猪油,我猜) 小火细煨不知多久才成的一锅鲜汤。不幸我不吃鱼,并不知道这两种鱼吃起来味道究竟有什么大不同。前两年回国,听说北京在流行完不知道哪个地方的特色菜之后转向了酸汤鱼,很为贵州菜高兴了一阵。也许因为川菜影响太大的原因吧,贵州菜一直不为外人所知。但转念又想,能在北京传开,那么说这菜已经变了味。
不知道山西人的酸是怎么来的。但我对贵州的酸深有体会。首先,贵州的土壤是酸性的。贵州红土,这我在地理课上学到,记得当时解了大大一个疑问。因为每年夏天买水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是甜的。李子是酸的,桃子是酸的,青枣儿又大又面又酸。最恐怖的是杨梅,一个个红得要发紫,绝对已经熟透,看上去非常甜蜜多汁的样子,但拈起一个放在嘴里,才知道牙都要倒了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一边打字一边思杨梅而生津,这么多年了,大脑某个片区仍然记忆犹新,可见其威力。贵州人买了新鲜杨梅不是要吃的,而是拿去煮,煮完后水里放糖,晾凉后做解暑的饮料。而煮过的杨梅酸性不减当年,仍然保持风骨吃不得。记得我娘说她第一次去贵州的时候买不到醋,到商店里去问,那时售货员态度正在恶劣状态,喋喋不休地反问:醋,醋,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醋。他们大概真不需要醋。酸白菜,酸圆白菜(他们叫莲花白),酸豇豆,酸萝卜,酸辣椒。。。家家都有泡菜坛,一坛一坛酸的是各式各样的蔬菜。我大学暑假期间回家,正在流行酸蒜苔,我娘的朋友每去我家必带一袋子给我,一来我娘手下毛糙,而酸菜是见不得一点而油星的,我娘每酸必坏,后来干脆罢手,虚心接收众友馈赠;二来那位阿姨大概是有小辈自远方来,爱我酸菜,宁不说乎的心理吧。贵州人极要面子而且好客,因此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虽然多是外来人口,长久了,也渐渐沾染了那些习惯。
已经很长了。看来一下子是说不完了。我也是,一说吃就激动到不得了,口沫横飞。
下回书再说吧。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